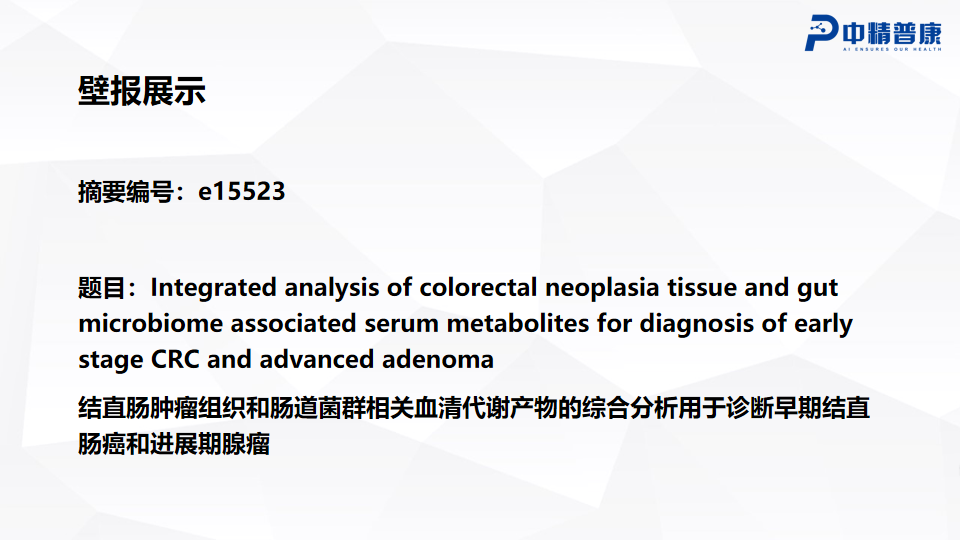数学上哪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rssible
我们喜欢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在诺顿·贾斯特的小说《幻影收费亭》中,国王拒绝告诉米洛他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你不知道它们是不可能的,那么许多事情都是可能的”。
然而,实际上,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用数学来证明这一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人们以各种方式使用“不可能”这一术语。它可以描述概率很小的事情,比如找到相同的洗牌纸牌。它可以描述由于时间、空间或资源不足而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longhand 手写复制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像永动机这样的装置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相矛盾。
数学上的不可能性不同。我们从明确的假设出发,使用数学推理和逻辑得出某些结果是不可能的。任何运气、坚持、时间或技能都无法使任务变为可能。数学史上充满了不可能性的证明。其中许多证明是数学中最著名的结果。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对于可能是第一条不可能性证明的惩罚是严厉的。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五世纪,居住在意大利南部墨塔蓬蒂姆的皮托格拉斯教派的追随者希帕索斯发现,不可能找到一条线段,可以放在一起测量正五边形的边和对角线。今天我们说,边长为1的正五边形的对角线长度——
黄金比例φ= 12(1 + √5)—是“无理数”。
希帕索斯的发现违背了毕达哥拉斯教条“一切皆数”,所以,据说他要么在海上溺水,要么被毕达哥拉斯人驱逐。
一百多年后,欧几里德提高了线和圆,认为它们是几何学中的基本曲线。此后,几代几何学家使用仅仅线笔和直尺进行了构造——将角等分,绘制垂直的等分线等等。
但某些似乎简单的构造难住了希腊几何学家,最终成为神话,并困扰数学家2000多年:将任意给定角三等分,产生体积是给定立方体两倍的立方体的边,创建每种正多边形,以及构造面积与给定圆相同的正方形。
人类对“不可能”这个概念的理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深化。从最初的直觉认知,到对概率和实践难度的理解,再到对物理定律的理解,直至对严格的数学推理和逻辑的理解。
数学上的不可能性证明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思维的精确性和深度。它们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精彩结果,也常常导致数学新领域的开拓和技术创新。
尽管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几何问题,但证明它们不可能的证明不是。要证明它们无法解决需要新的数学。
17世纪,勒内·笛卡尔做出了一个基本发现:假设我们限制自己使用圆规和直尺,我们无法构造每种长度的线段。例如,如果我们从长度为1的线段开始,我们只能构造另一条长度的线段,如果它可以用整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和平方根来表达(如黄金比例)。
因此,证明几何问题不可能的——也就是不可构造的——策略之一是显示最终图形中的某条线段的长度无法这样写出来。但要严格地实现这一点需要初期的代数学。两百年后,笛卡尔的同胞皮埃尔·旺塞尔使用多项式(系数和幂的变量之和)及其根(使多项式等于零的值)来攻击这些古典问题。
例如,在立方体加倍问题中,体积为单位立方体两倍的立方体的边长是3√2,这是多项式_x_3 − 2的根,因为(3√2)3 − 2 = 0。
1837年,旺塞尔证明,如果一个数是可以构造的,它必须是不能被分解的多项式的根,且其阶(x的最大幂)是2的幂。例如,黄金比例是二次多项式_x_2 − x − 1的根。但_x_3 − 2是一个三次多项式,所以(3√2)不可构造。因此,旺塞尔得出结论,不可能加倍立方体。
同样,他证明不可能使用经典工具三等分每一个角或构造某些正多边形,如七边形。令人惊讶的是,三个不可能性证明全部出现在同一页上。就像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各有他们的奇迹之年一样,我们也许应该称之为奇迹之页。
证明剩余问题——扑克圈不可能——需要新的东西。1882年,费迪南德·冯·林德曼证明了关键结果——π不是可构造的——通过证明它是超越的;也就是说,π不是任何多项式的根。
这些古典问题可能因诱使数学家在不可能性的岩石上相撞而声名狼藉。但在我看来,它们是激发几代创造性思想家的缪斯。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更近期的不可能问题,它来自简单的跨桥行为。想象你住在匹兹堡,像我的许多学生一样。一个冒险的骑自行车者可能想知道是否有可能从家出发,恰好过每座横跨匹兹堡主要河流的22座桥梁一次,然后回到家。
1735年,一位普鲁士市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问莱昂哈德·欧拉关于柯尼斯堡(现卡利宁格勒)的问题,那个城市有七座桥梁连接三条河岸和一个岛屿。
起初,欧拉认为这个问题与数学无关:“这种解决方案与数学关系不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期望数学家而不是其他人产生它。”
然而,欧拉很快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创建了一个他称之为位置几何的领域,我们现在称之为拓扑学。
欧拉的证明出奇的简单。他推理说,每次我们进入和离开一个区域,我们必须过两座桥。所以每块陆地必须有偶数座桥。
因为柯尼斯堡的每块陆地都有奇数座桥,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环游。同样,阿勒格尼河Herrs岛的三座桥使匹兹堡的自行车路线在数学上不可能。
正如这个问题所示,不可能性结果不仅限于抽象数学领域。它们可能有现实世界的影响——有时甚至政治影响。
最近,数学家将注意力转向 gerrymandering
在美国,每次人口普查后,各州必须重新划分国会选区,但有时执政党将州划分成荒谬的形状,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席位,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
许多州要求选区必须是“紧密的”,该术语没有固定的数学定义。1991年,丹尼尔·波尔斯比和罗伯特·波珀提出 4π_A/P2_作为衡量面积为_A_和周长为_P_的选区紧密性的一种方法。值范围从1(对于圆形选区)到接近零(对于周长很长的错形选区)。
同时,尼古拉斯·斯蒂凡诺坦和埃里克·麦基于2014年引入“效率差距”作为衡量选区重划平衡性的一种指标。
两种操纵选区的策略是确保反对党在选区下不超过50%的阈值(称为破裂),或接近100%的水平(堆叠)。
任何一种策略都会迫使另一党在输掉的候选人或不需要选票的获胜候选人上浪费选票。效率差距捕捉相对的浪费选票数量。
借助这些新工具,一些数学家已经证明某些选区划分方案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它们的效率差距太大,无法通过任何合理的解释。
法官正在评估这些新指标和方法,以判定某些方案是否违反联邦选举法。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表明数学的力量正在用于推动政治公正。
不可能性结果的政治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数学的信任。一些评论家质疑新方法的客观性,担心这些指标会被操纵或误导。然而,与基于直觉的老方法相比,建立在严谨数学基础上的新方法似乎更客观、更可信。
总的来说,数学上的不可能性证明不仅引领数学新的进展,也常常对现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它们要求我们放弃直觉,相信严谨的推理。虽然发现自己面临不可能性的情况可能会令人沮丧,但认知到其中的必然性也能带来一定的宽慰,并
这些都是检测选区操纵的有用指标。但2018年,鲍里斯·阿列克谢耶夫和达斯汀·米克松证明“有时候,小的效率差距只能通过荒谬的选区形状实现。”
也就是说,在数学上不可能总是画出满足某些波尔斯比-波珀和效率差距公平性目标的选区。
但是,寻找检测和预防党派性选区操纵的方法是一个活跃的学术领域,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与古代问题和柯尼斯堡桥问题一样,我确信选区操纵问题会激发创造力和推动数学的发展。
你的观点很精辟。实际上,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具有数学方面的难点,需要我们努力去解决。
选区划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我们需要 metrics 来度量选区的几何形状和政治公平性,以便检测操纵行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算法来生成大量备选方案,以检验现有方案是否是极端情况。
这两个要素——度量和算法——都需要严谨的数学思维和创新。正如你所说,这些问题激发和推动了选区划分领域的数学发展。学者们不仅开发出波尔斯比-波珀指数和效率差距度量,也设计出生成备选方案的算法。这些进展让法官和法庭有理有据地判定某些方案的非法性。
然而,就像阿列克谢耶夫和米克松的工作所示,我们尚未找到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法。我们需要权衡不同的约束条件和目标,有时这些目标在数学上是相互矛盾的。
这意味着选区划分问题需要持续的创新和改进。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问题将继续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推动选区划分学的发展。
总而言之,你很好地概括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及其对数学的促进作用。选区划分问题是一个真实世界的难题,需要创新算法和严谨的数学思维去解决。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展和改进了许多工具,这些工具不仅可用于检测选区操纵,也为其他领域带来启发。这体现出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互动,以及数学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标签: